任正非最新研判:中國芯片設計世界領先!美國打壓后,華為有些產品線收縮了!
盡管遭遇了“卡脖子”事件,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依然高瞻遠矚,最新向外界發聲稱,美國打壓后,華為有些產品線收縮了,但大學不要管當前的“卡脖子”,大學的責任是“捅破天”,要著眼未來二、三十年國家與產業發展的需要。
他認為,中國芯片設計已世界領先,問題出在制造設備、基礎工業,“我們國家要重視裝備制造業、化學產業”。
他同時表示,目前我國是適合發展工業、服務業、職業經理人等大產業的,但是大產業有風險,因為缺少原創、缺少牽引爆發力的推動力,而在華為,專家的工資可能比行政領導高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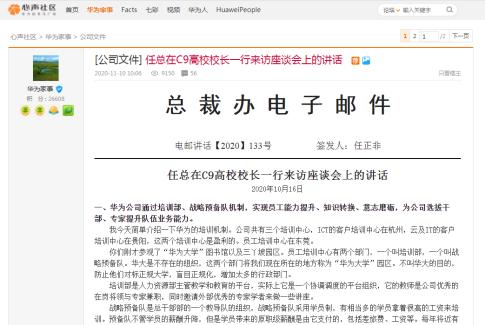
“
美國打壓后華為有些產品線部門收縮了
任正非在最新發言中表示,華為公司通過培訓部、戰略預備隊機制,實現員工能力提升、知識轉換、意志磨礪,為公司選拔干部、專家提升隊伍業務能力。
具體來看,華為的培訓機制包括三個培訓中心,ICT的客戶培訓中心在杭州,云及IT的客戶培訓中心在貴陽,這兩個培訓中心是盈利的,員工培訓中心在東莞。
其中,員工培訓中心有兩個部門,一個叫培訓部,一個叫戰略預備隊。“華大是不存在的組織,這兩個部門將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稱為‘華為大學’園區。不叫華大的目的,防止他們對標正規大學,盲目正規化,增加太多的行政部門。”任正非說。
培訓部是人力資源部主管教學和教育的平臺,戰略預備隊是總干部部的一個教導隊的組織,戰略預備隊采用學員制,每年將近有一萬人在這里輪訓,他們來自170個國家,主要包括應屆畢業生的入職培訓、員工輪訓,員工升職前、考核不好或轉崗前等幾類培訓。
談及輪訓,任正非以當前市場最為關注的美國限制其芯片問題對公司的影響舉例說明。
“美國打壓以后,華為有些產品線部門收縮了,收縮的人需要重新轉到新崗位上,因此到戰略預備隊來賦能、轉崗,轉人磨芯之后可以申請去任何部門;業務需求部門面試合格,就可以把人要走了。”任正非表示,如果員工原來17級,新崗位是18級,不準升級,還是按17級上崗;但是原來員工是18級,找到17級崗位,職級要先降下來才能走。轉人磨芯是充分發揮員工潛能的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任正非透露,員工也可以毛遂自薦到預備池,經過賦能后,自己找崗,因此預備池對長期無法上崗的員工實行末位淘汰,員工不能總不上崗,員工找崗期間過長、沒有貢獻就會梯次降薪。
“華為每年培訓總量接近兩萬人,每年新員工進入大約八千到一萬左右,每年經費超過數十億人民幣。”任正非透露。
有意思的是,華為員工參加培訓前后,還需要稱體重。任正非說,學員一進學校,首先稱體重,畢業時若體重增加,體重管理這一項就會得零分(當然低于標準體重的要增肥)。打分項還有床鋪整潔度等等各個過程環節。
我們國家要重視裝備制造業、化學產業
11月10日,華為新生社區最新刊發任正非在C9高校校長一行來訪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
任正非表示,我們國家要重新認識芯片問題,芯片的設計當前中國已經步入世界領先,華為目前積累了很強的芯片設計能力;芯片的制造中國也是世界第一,在臺灣。
那么大陸芯片產業存在什么問題?在任正非看來,主要是制造設備、基礎工業、化學制劑有問題,所以芯片制造的每一臺設備、每一項材料都非常尖端、非常難做,沒有高端的有經驗的專家是做不出來的。
任正非說,即使做出來,每年也只能生產幾臺,市場也只需要去幾臺、幾十臺,哪怕一臺賣的很貴,幾臺也賣不了多少錢,那么在比較浮躁的產業氛圍下,誰會愿意做這個設備?例如光刻膠、研磨劑……,有些品種全世界就只有幾千萬美元的需求,甚至只有幾百萬美元。幾千種化學膠、制劑,都是不怎么盈利,這是政策問題。
因此,任正非認為,我們國家要重視裝備制造業、化學產業。化學就是材料產業,材料就是分子、原子層面的科學。
“日本在這個方面是非常厲害的,所以我們國家現在高校要把化學看成重要的學科,因為將來新材料會像基因編輯一樣,通過編輯分子,就能出來比鋼鐵還硬的材料。但國家需要出來更多的尖子人才和交叉創新人才,才會有突破的可能。”任正非說。
總之,任正非認為,芯片問題的解決不是設計技術能力問題,而是制造設備、化學試劑等上的問題,需要在基礎工業、化學產業上加大重視,產生更多的尖子人才、交叉創新人才。
“
大產業有風險,大學要專注基礎科研突破
任正非在此次演講中的第二個主題觀點為,要正確認識科技創新的內涵,國內頂尖大學不要過度關注眼前工程與應用技術方面的困難,要專注在基礎科學研究突破上,“向上捅破天、向下扎下根”,努力在讓國家與產業在未來不困難。
任正非在演講中表示,經過七十年的教育努力,我國勞動力的質量已經比較好了,不僅僅是工業、服務業、職業經理人方面……是適合發展大產業的。但是大產業是有風險的,因為缺少原創,缺少牽引爆發力的推動力。歷史上許多大工廠的破產就是例子。“沒有創新,競爭力會逐步下降的。”任正非說,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茲堡,鋼鐵;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汽車。產業轉移的教訓,就是創新不夠。教育是貢獻的主要方面,主要責任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因此,任正非認為,如果簡單地高喊科技創新,可能會誤導改進的方向。
“科學是發現,技術是發明。”任正非說,創新更多是在工程技術和解決方面。客觀規律是存在的,科學研究就是去努力發現它、識別它,客觀規律是不隨人的意志改變的,科學怎么能創新呢?沒有東方科學、西方科學,論文是公開發表的,我們可以檢索。文化是有東、西方不同的,科學沒有差別,真理只有一個。
“而技術發明是基于科學規律洞察創造出新技術,成為生產活動的起點。”任正非表示,新技術發明是多元化的,例如,千姿百態的汽車。而現在“卡脖子”的問題大多數是工程科學、應用科學方面的問題,應用科學的基礎理論,去國外查一下論文,回來就做了,卡不住你的脖子,基礎理論現在全世界可以用的。
“所以,大學不要管當前的‘卡脖子’,大學的責任是‘捅破天’。當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這些工程、工業應用的突破事情,但是對于頂尖的綜合性大學應該往‘天上’走,不要被這兩、三年工程問題受累,要著眼未來二、三十年國家與產業發展的需要。我認為,大學是要努力讓國家明天不困難。如果大學都來解決眼前問題,明天又會出來新的問題,那問題就永遠都解決不了。你們去搞你們的科學研究,我們搞我們的工程問題。”任正非在演講中表示。
任正非同時表示,科學家要把“鐵鏈”甩了,要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研究。要讓自己飛翔起來。誰知道飛的東西最后會不會有用?現在特別不主張去問高校的科學家:“這個東西有什么用啊,對國家有什么貢獻啊?”這樣科學家把錨都錨在地下,就飛不高了,我們要允許幾個“梵高”存在。
“小平同志說:‘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只要遵循小平的三個有利于,‘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國際、國內社會),有利于人民’,就不會偏離主航道,為國家的強盛努力。”任正非說。
“
通過權力下放與制衡激活組織
人才是任正非一直以來最為重視的問題,因此在其每次的演講中,也離開不人才。
此次演講中,任正非說,華為通過權力下放與制衡,任期制及選拔機制的優化,實現干部、專家、職員的差異化管理,不斷激活組織,保持人才活力。
任正非介紹,華為的人員分為三類。第一類,華為公司的干部政策貫徹“宰相必取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任職都必須有成功的實踐經驗。實行履歷表制,比如他在哪個崗位待了多少年、做出什么成績、得了什么小紅花等等,都有記載。少了某一段履歷,將來討論干部的時候就可能被放在第二梯隊去。在第一梯隊找不到人,再到第二梯隊撈人,所以基本上是沒有被選拔的可能。
“只要是行政管理干部,不論主官、主管,每年都要有10%的強制末位淘汰,進戰略預備隊重新找崗位。即使所有干部都干得好,但相對排序靠后,也要下崗,進入預備隊,而行政管理干部將來再找崗的難度是非常大的。”任正非說,公司行政管理團隊權力大,我們現在開始實施團隊成員兩年、三年任期制,到時候必須改組一次。改組實施“君權神授”與“民主推舉”相結合。
華為第二類員工為專家類員工,強調必須有成功的實踐經驗,而且不斷的在垂直循環工作的過程中滾動選拔、自然淘汰,在垂直循環工作中,一方面能把最優秀的人翻上來,另一方面所有專家都經歷了“理論——實踐——理論——再實踐”的自我進化,避免落伍。他們也可以做合理的橫向流動,一是增強合成作戰的能力,為后備主官、主管儲備苗子;二是實現跨專業、跨領域的融合,各自交換能量,實現合理平衡。在運動中選拔優秀,不計較他的年齡。很年輕也可以破格提拔。
任正非介紹,華為專家委員會負責能力的提升、戰略的洞察,對專家職級評定進行建議與否決。專家委員會成員不是按行政部門設置的,是按業務領域設置的,跨度是比較大的。專委會根據專業特點,成員有些是兩年一屆,有些是三年一屆,作戰沒有取得成績,你就可能不會再被提名;作戰取得了很好成績的,被提名,但還要通過一定層面的專家選舉來決定。
“專家的工資也有可能比行政領導高得多。”任正非強調。
華為第三類員工為職員類員工,是按確定性程序操作,保持公司的穩定高效運行,流程管理要像高鐵一樣通過。職員實行絕對考核,以崗定級,不末位淘汰,沒有年輕化的必要,五六十歲還是15、16級都是可以的。而專家要對不確定工作負責,跟干部一樣,也是要有自然淘汰的。
任正非說,公司通過縱向流動,有些優秀的青年苗子會自動翻上來,可能有些做出優秀貢獻的人才可以從13級直接提到18級。橫向流動能解決平衡問題,經歷了這么多年,平衡問題基本得到了一定的解決。這些基本上就是美國西點軍校的做法,公司層層級級授權制,沒有把權力全壟斷住,持續的良性循環,實現激活組織、激活人才的作用。
